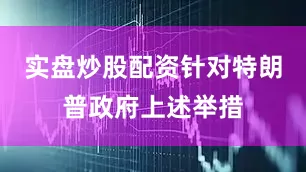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想必广为人知,许多人都能够熟记于心,这毕竟是教材中必背的经典之作。诗中的“大渡桥横铁索寒”一句,正描绘了长征路上那场惊心动魄的“飞夺泸定桥”战役。
毛主席曾对斯诺言道:“穿越大渡河,实乃长征历程中至关重要的节点。若红军在此遭遇败绩,其存续将岌岌可危。”
显而易见,在当年的大渡河之滨,红军所遭遇的,实则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对彼时红军所遭遇的艰难险阻有所了解,便不难领会毛主席所言非同小可,绝非夸张之词。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一个基本常识。实际上,“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指的是同一历史事件,目的都是为了跨越这道大渡河,只是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策略。简单来说,起初的计划是从安顺场乘船渡河,但这一方案未能如愿,随后便转而选择了通过泸定桥来穿越大渡河。
然而,“飞夺泸定桥”一事始终伴随着诸多质疑之声。这些质疑的产生,原因并不复杂,只需浏览下图便一目了然。

观察图片可知,光滑的铁链上站立都颇为不稳,然而红军的敢死队仅二十二名勇士,却能迎着敌军的密集火力勇往直前。这显然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险地,若在桥头部署一挺机枪,岂不是让无数士兵徒增牺牲?这简直就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绝境。
质疑无妨。
然而,事实不容置疑,正是红军成功夺取泸定桥,使得局势得以扭转,转危为安。
红军究竟是如何成功突破的?这其中确实涉及到众多复杂因素。
详细论述此历史。
壹 强渡大渡河
1935年三月,红军历经“四渡赤水”的艰苦奋战,成功突破蒋介石布下的重重包围。
我们先前曾提及四渡赤水之战,毛主席此举可谓是将红军从绝境之中成功拯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红军可以从此安枕无忧。相反,红军面前摆着的,是另一个险恶的绝境——那就是大渡河。
先看红军长征路线图。

自血战湘江启程,历经四渡赤水,勇闯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穿越草地,回顾过往,每一战都险象环生,稍有不慎,便可能导致全军覆没的悲剧。
在那段岁月,那支红军队伍若非凭借其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每道关卡在今日回顾,无不显现出必死的险境。正因如此,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都享有极高的赞誉。
如上图所展示,红军在成功巧渡金沙江之后,为了与红四部队汇合,首要任务是横渡大渡河。
实际上,关于能否成功穿越大渡河,众人心底并无确切把握。
大渡河的两岸绵延着巍峨耸立的高山,水流湍急,深不见底,河床之上遍布着错落有致的嶙峋岩石,交织出无数的涡流漩涡,哪怕是轻盈的鹅毛投入其中,也即刻沉没河底。由此可见,这样的自然条件实乃桥梁建设之大忌。
然而,彼时红军所遭遇的境况异常严峻:后方有薛岳指挥的十万中央军紧追不舍,前方则是险象环生的天险大渡河,川军刘文辉部在此布置了严密的防线。与此同时,另一支川军杨森部亦正急速赶往大渡河防线。在如此劣势下,红军仅有2万余人,却须面对装备精良、兵力达15万的国民党军队。
形势愈发明朗。红军若能在追兵抵达前成功渡过大渡河,便能暂时解除危机,喘息片刻。若未能如愿渡河,以敌军之强大兵力,结局不言而喻,唯有全军覆没一途。
此类情形并非首例。回溯至72年前的1863年五月,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便是在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遭遇了全军覆没的命运。蒋介石深知红军难以逾越的大渡河天险,便下令川军刘文辉部加强防御,意图将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回顾过往,问题实则源自刘文辉,这一点我们稍后再作详述。
红军奋勇挺进大渡河,红一军团下辖的第一师第一团(以下简称红1团)肩负先锋使命,在前面开路。该先遣队的指挥官为刘伯承,政治委员则是聂荣臻。
刘帅,一位地道的四川人氏,在投身革命之前,曾与熊克武共事,因此声名鹊起,成为川中赫赫有名的将领。他之所以担任先锋,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地形了如指掌,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在川军中他拥有几位熟识的老友,这层关系说不定在关键时刻便能发挥关键作用。
刘帅确实派上了大用场。
自西昌至大渡河畔,红军当时面临两条路线可供选择。
西昌至越西,经大渡河富林渡口。此路称“西越路线”。
西昌至冕宁、大渡河安顺场渡口。这是“西冕路线”的山路。
众所周知,平坦的大道易于行走,常规思维亦认为红军必会选择此道前进。即便是精于微操的蒋委员长,亦持有此一见解,因此他将川军的主力部署于此路,意图进行有效堵截。
毛主席堪称心理学界的巨匠,自是深谙“预料你的预料”之道,因而反其道而行,毅然选择了“西进路线”,即迂回山道。
这无疑是一步充满风险的棋局。选择西冕路线,不仅山路崎岖难行,更关键的是,必须穿越彝民聚居区。
近年来,彝民屡遭汉人驱逐至深山幽谷,对汉人的怨愤不言而喻。加之彝民大多仍处原始社会阶段,即便无怨,亦难免将你掠夺一空。
显而易见,彝族民众遇到突如其来的汉族军队,岂会轻易放行?
直接联络是否可行?实则不然,薛岳的部队正紧追不舍,红军并无闲暇亦无需与彝族部族过多纠缠。
红军坚持的原则,即在通过彝民区域时,秉持和平相处之道,绝不主动反击,既不对抗也不恶言相向。
然而,彝民对此并无理会。一旦先遣队的工兵连踏入彝民领地,便遭缴械,衣物亦被剥去。
此时,刘伯承的智慧显现无遗。他先是巧妙地拉近关系,继而利用土司小叶丹渴望借助红军力量击败其他土司的愿望,与其进行了“歃血为盟”的仪式,从而结为兄弟。
何须多言?兄弟之间岂能相互刁难。红军主力紧随先遣部队,顺利穿越了彝族地区。
毛主席对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之举给予了高度赞誉,他指出,即便诸葛亮需历经七擒七纵之策方能收服孟获,刘帅却仅凭一杯鸡血酒便轻松化解。
刘帅轻描淡写地回应道:“那又何足挂齿,我曾委以重任,任命小叶丹同志为‘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长。”
穿越彝民区域之后,我们的下一站便是安顺场。红军的既定计划便是自安顺场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渡河。
刘伯承在旅途中心情颇为不安。他深知安顺场渡口的河水汹涌,桥梁搭建几无可能,唯有依靠渡船一途。然而,刘文辉的川军并非易与之辈,难道会将渡船轻易留在河岸旁?
事实确如刘伯承所担忧。
刘文辉虽在安顺场部署了一定的防御力量,但其核心防御重点无疑落在了“西越路线”上。因此,安顺场两岸仅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值得一提的是,该营的营长韩槐阶身为当地袍哥首领,他所率领的队伍并非正规军,而是由袍哥组织改编而来。由此不难想见,其战斗力水平究竟如何。
本来蒋介石的命令是在安顺场渡口坚壁清野,全部烧光,让红军毫无借力。当地有个恶霸叫赖执中,是刘文辉24军的一个营长,由于安顺场的大半房屋是他的,坚决不同意烧街。他的意思倒也不是不能理解:若是红军不选择通过安顺场,岂不是白白损失了财产?
韩槐阶本为江湖人士,自不愿与赖执中结怨,然军令如山,最终双方商议妥当,决定派遣探子先行侦察。一旦确认红军确有动向,直指安顺场,便即刻执行火烧街头的策略。
赖执中暗中留有后手,于安顺场藏匿了一只小舟,以防红军到来时,能乘坐此船逃至北岸。然而,他未曾料想,正是这艘小舟,最终为红军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此刻,刘亚楼与左权指挥红5团奔赴距安顺场三十公里的大树堡,在当地积极开展扎筏造船的工作,场面一片繁忙。实则,这乃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迷惑敌人视线之计,用以诱使敌方分散注意力。
韩槐阶不幸中了圈套,误以为红军将循大树堡渡河,加之当晚暴雨如注,便断定红军断然不会前来,于是便沉迷于唱戏、饮酒、打麻将,全然放松了警惕。
1935年5月24日夜晚10时,杨得志率领的红一团在雨中抵达安顺场。一场迅猛的冲锋便击溃了守军,袍哥部队不堪一击,战斗在不到三十分钟内迅速结束。
刘伯承对于攻占安顺场并无忧虑,他真正忧心的是能否寻觅到船只。尽管蒋介石的指挥能力存疑,但他实施坚壁清野的恶劣手段却是层出不穷。
谁料想,那位看似微不足道的恶霸赖执中,竟在无意之中,为我国革命事业贡献了巨大力量。他原本预备逃跑的船只未曾启航,便不幸落入了敌手,被俘获。
凭借这支唯一的小船,一营营长孙继先率领十七位勇士,分作两批奋勇冲锋,终成功抵达对岸。他们,正是闻名遐迩的“大渡河十八勇士”。
提及此事,恐怕有人会心生异议。难道十八人乘坐小舟就能成功穿越敌军密集的火力封锁?这川军的战斗力究竟如何?
此含两要素。
此渡口至彼岸距离不远,约莫三百米之遥,尚在火力射程之内。红军凭借占据优势的火力,有效压制了川军的攻势。红军阵营中,有一位声名显赫的炮手——赵章成,他以仅有的三发炮弹,成功摧毁了对岸的防御工事,弹无虚发,无一浪费。此举直接击溃了守军士气的防线。
赵章成,这位炮手的佼佼者,天赋卓绝,其对于成功强渡大渡河的功勋不可磨灭。建国之后,他更是荣任炮兵副司令员的要职。
再者,如前所述,对岸的守军乃是一支袍哥队伍,平日里欺压百姓、收取保护费尚可,但若真到了拼命的地步,他们的逃跑速度比兔子还要迅捷。面对红军那种不要命的战斗风格,他们顿时感到不知所措。一见红军有人成功登陆,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保命最为重要,于是急忙逃窜。
在成功突破大渡河之后,接下来的任务便是探讨如何让主力部队顺利渡河。实际上,渡河的途径不外乎两种:要么乘坐船只,要么搭建桥梁。
两种方法均无效。
红军在对岸仅觅得两艘小舟。凭借这三艘简陋的船只,红一团不懈努力,直至5月26日方才将全体人员成功输送至对岸。刘伯承一番计算后得出,若以如此进度,红军数万大军欲借助这几艘小船渡过大渡河,至少需耗时一个月。
此刻,薛岳部队与杨森部队正急速向安顺场进发,距离目的地仅余数日行程。显而易见,乘坐船只渡河的方案已不可取。
既然船只无法依赖,便转而尝试搭建桥梁,纵使无法成功,亦需想方设法。然而,事实却无情地证明,桥梁是无法搭建的。渡口处水深流急,桥梁未及稳固,便已被汹涌的急流冲得无影无踪。
刘伯承陷入了沉重的焦虑,心中充满了忧虑。红军难道真的会步石达开的后尘,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吗?
此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齐聚安顺场。在听取刘伯承同志的详细汇报后,众人皆已意识到,乘坐船只横渡大渡河的计划已无实现的可能。
毛泽东与几位权贵商榷一番,毅然决然,不再于安顺口渡口滞留时日,决定另辟蹊径。这条路是泸定桥,位于安顺场西北方向。
红1师及军委干部团全体成员,搭乘三艘小船,成功渡越大渡河,构成右翼纵队。该纵队由刘伯承将军和聂荣臻将军共同指挥,沿着大渡河的右侧河岸,向泸定桥方向挺进。红2师和红5军团组成左翼纵队,由林彪将军统率,沿着大渡河左侧河岸,亦向泸定桥进军。中央军委及其主力部队则跟随左翼纵队,从河的左侧同步前进。
大意如下图所示。

看到这儿基本就明白了,飞夺泸定桥之役,实则形成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战术布局,正是这种左右夹击的策略,成为了左翼部队成功夺取泸定桥的决定性因素。
寥寥数语,却蕴含着深刻的意义。此时此刻,关于能否攻克泸定桥,众人心底尚存疑虑。毕竟,川军在 大渡河沿线部署了重兵,红军能否顺利抵达泸定桥,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加之,泸定桥的宽度仅有3米,若川军在桥头实施强有力的阻击,红军在如此狭窄的桥梁上发起冲锋,其难度显而易见。
因此,毛泽东实际上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他特意将干部团编入右路纵队,其目的在于,一旦泸定桥无法攻克,便让刘伯承等人在川西地区积极发展群众力量,建立根据地,干部团的随行便是为此考虑。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主力则在川康地区持续作战,以期寻找新的机遇,实现北渡黄河的战略目标。
毛主席惯用的战术往往采取“以宽待人”的策略,在战略层面轻视敌人,而在战术层面则高度重视,并为此精心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然而,事实却表明,红军对于刘文辉部队的战斗力预估过于乐观。
贰 飞夺泸定桥
在红军左右两路部队抵达泸定桥之际,我们不妨先探讨一下川军的相关情况。这对于深入理解红军成功飞夺泸定桥的历史意义至关重要。
四川军阀之众,在全国范围内堪称首屈一指,曾一度繁衍至百余人之众。究其根源,不可不提及同盟会元老熊克武。
在辛亥革命的风云变幻之际,熊克武于四川掀起革命浪潮,一时之间,他成为了该省的实际统治者。然而,资金匮乏,甚至连士兵的军饷都无法发放。面对这一困境,熊克武创设了“防区制”,授意各路军头自行设法筹集款项与粮食。虽然这一举措暂时解决了财政难题,但其弊端亦日益显现,各地的军头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
为争夺地盘,由此拉开了一场长达四十余年的军阀混战。然而,四川的军阀虽然看似战火纷飞,实则如同儿戏一般。甚至有军阀在交战时,周围的百姓竟然如同观看街头表演一般围观。每当农忙时节,各路军阀都会默契地停止战斗,各自回家投身于农业生产。正因为如此,尽管四川军阀间的内斗持续多年,但四川的人口不仅未见减少,反而略有增长。
又一显著特征是僧多粥少,民众数量有限,却需负担众多军阀的生活开销,由此可见,这些军阀普遍经济拮据。多数军阀所拥有的武器装备极为落后。
随时光流转,刘湘等一众军阀纷纷投靠了蒋介石,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的行列。在老蒋的扶持下,刘湘终获胜利,登上了四川王的宝座。然而,那些败北的小军阀并未就此罢休,诸如杨森、邓锡侯、刘文辉之流,即便认输,也仍逃至偏僻之地,继续维系着他们的势力。
本文聚焦于主角刘文辉,他与刘湘之间系出同宗,为叔侄关系。刘文辉年长刘湘六岁,尽管如此,在辈分上,刘湘需尊称刘文辉为叔。
原本刘文辉乃刘湘亲手栽培之才,然受时局所困,终亦走上了独立之路。及至势力渐强,便与刘湘在四川之霸主地位上展开了激烈角逐,以至于与亲侄子也刀兵相向。
终究,刘文辉未能击败刘湘,转而退守川康,过着隐忍的日子。而刘湘亦虑及通过刘文辉制约邓锡侯、杨森等人,便未予穷追猛打,时光便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尽管统称为川军,实则内部派系林立。当年红军四渡赤水,横渡长江之际,所遭遇的阻截,正是刘湘所率领的川军。而如今,在大渡河的两岸,展开阻截的,则是刘文辉麾下的部队。
无论是对刘湘,亦或是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人而言,他们共同持有一种观点,即若能彻底消灭红军自是上策,若不能,也务必将其遏制在己方势力范围之外。此中的道理并不繁复,众人皆知蒋介石所行乃“一石二鸟,驱狼吞虎”之策,既欲剿灭红军,又意图鲸吞土地,王家烈之败便是明证。
言辞至此,我主要欲阐明的是,刘文辉所率领的川军不仅装备简陋,其战斗力亦不尽如人意。加之军队将领各有私心,这无疑为红军创造了可乘之机。
言归正传,再谈红军。
林彪所率的红军左纵队肩负着攻克泸定桥的重任。安顺场至泸定桥的全程约计320里路程。
得知红军自安顺场挺进泸定桥的战报后,蒋介石即刻获知了这一讯息。于是,他特地赶到成都,对刘文辉部下达了严令,要求他们务必死守泸定桥,同时督促各路追兵加快步伐,迅速向泸定桥靠拢。在临行前,老蒋特意叮嘱刘文辉,一旦形势危急,不惜将泸定桥的铁索炸毁。
对于老蒋而言,既然安顺场未能令红军沦为“石达开第二”,那么他势必要在泸定桥一役中彻底消灭红军。
局势愈发紧迫,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紧随,此时此刻,双方竞速成了决定性的较量。能否在国民党追兵抵达之前成功跨越泸定桥,成为了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转折。
红4团作为左纵队先锋,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队疾驰向泸定桥进发。然而,川军的防守步步紧逼,队伍不得不边战边行。直至5月28日凌晨,队伍仅前进了80里。
拂晓五时,红4团正欲稍作喘息之际,林彪的指令迅速传来:鉴于追兵将至,刘文辉的第4旅亦正向泸定桥进发以提供支援,我们必须抢在敌军之前抵达泸定桥。军委明确指示,必须在次日夺取泸定桥,因此,部队务必在次日上午抵达泸定桥的南岸。
黄开湘与杨成武览图而惊。此处距泸定桥尚有240里之遥,而要在短短一日一夜间跨越这240里路,途中山路险峻,敌军关卡重重,此任务几近于不可能完成。
然而,红军已无退路可寻。对红4团而言,唯有竭尽全力,奋勇向前。
为了振奋士气,尽管杨成武因腿部受伤本应骑马行军,他却毅然决然地放弃骑乘,率先走在队伍的最前方。伴随着全体将士高呼“奋勇前行,抵达泸定桥”的激昂口号,队伍以迅疾的步伐向目标地点进发。
红4团在激战的同时且行且进,为了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甚至出现了与川军伪装同行,共同向前的奇异景象。5月29日的凌晨6点,历经一天的颠簸与挫折,红4团竟奇迹般地准时抵达了泸定桥。
红四团在红军历史上书写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奇迹,而纵观全球,这同样是一项罕见的急行军壮举。
5月29日午后四时,泸定桥攻坚战的全面进攻随即展开。
谈及此,有必要特别指出一点。在我们心中,泸定桥的形象通常是如下所示的。

泸定桥由十三根铁索紧密交织而成,两侧各安置了两根,桥面部分则由九根铁索构成,整体长度达到103米,宽度为3米,其上铺设着坚实的桥板。
教材中记载了飞夺泸定桥的英勇事迹,普遍提到川军先期拆除了桥面木板,仅留下13根裸露的铁链。这一举动令众多人感到困惑,毕竟泸定桥本身行走便极不稳定,如何在敌方火力猛烈的情况下成功跨越呢?
继而有部影片名为《勇士连》,其描绘的正是红军突击队沿光滑的铁索奋勇前行的壮丽场景,此举无疑旨在彰显红军战士的勇猛无畏。
事实并非全然如此。
根据刘文辉24军将领张伯言、杨学瑞等人的记载,桥板的确被抽走了一部分,但并未完全被移除。原因实则并不复杂。红军正急速行军,奔向泸定桥之际,川军第4旅38团亦在赶往泸定桥的路上疾行。抵达泸定桥的川军士兵早已筋疲力尽,加之当晚暴雨倾盆,众多士兵烟瘾发作,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抽桥板的进程异常缓慢。
仅至抽签过半之际,红四团的先锋部队已抵达对岸的桥头阵地。
依据张伯言的记载,对红四团何以能迅速攻克泸定桥,便一目了然。
红四团二连精心挑选出二十二位英勇的敢死队员,每位队员均装备了一支冲锋枪、一把锋利的马刀以及十二颗手榴弹。紧随其后的是三连,他们携带木板,突击队员们沿着铁索奋勇向前,随后铺设桥板以供战友们通行。
细心的朋友或许已经察觉,每个人手持一支冲锋枪?红军的装备竟如此精良?
确实,在那场飞夺泸定桥的激战中,红军所携带的武器装备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对川军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红军所装备的先进武器,无疑是得益于运输大队长的卓越贡献。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引进了大批德国制造的伯格曼冲锋枪,此枪素有“花机关”之称。这些枪械主要装备了嫡系部队班长及以上级别的士兵。在针对红军的围剿行动中,红军不仅缴获了大量的“花机关”,还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轻、重机枪。
经过湘江血战和四渡赤水的激战,红军的兵力有所减少,然而,他们手中的武器却得以保留。在人员减少而装备过剩的情况下,红军曾将那些陈旧、破损的武器予以销毁,并换装了新式武器。
关于川军的装备状况,前文已有提及。四川军阀普遍财力有限,其中刘湘的部队装备相对较好,而其他军阀的武装则相当陈旧。刘湘还封锁了长江航道,严格限制其他军阀从外部购置武器。因此,多数士兵所持的枪械多为四川本地制造,甚至包括一些古老的清朝汉阳造。这些枪械本身品质不佳,加之使用年限较长,膛线磨损严重,射程有限,射击时子弹散布范围广,精准度极低。
泸定桥的跨度一目了然,两岸相距约100米,尽在射程范围之内。在红军占据绝对火力优势的猛烈压制下,对岸的川军被击打得无法抬头。川军的那些破旧枪械,即便是对岸射击,也显得力不从心。
正如杨成武在其自述的回忆录中所述,“在曾庆林的指挥下,全团动用了百余挺轻重机枪,用以掩护夺桥及铺桥行动。”这样的装备配置堪称恐怖。然而,这恐怕并非红4团的常规配置,而是由其他数个团共同临时凑集而成。
在红军强大火力的猛烈打击下,2连连长廖大珠率领的突击部队勇猛直前,成功突破敌阵,抵达了桥头,进而进入了泸定城。尽管川军38团的团长李全山试图组织人员进行反击,但紧随其后的红军3连亦抵达泸定城,紧跟着,杨成武与黄开湘亦率主力部队迅猛跟进。
川军士气一落千丈,在红军的猛烈攻势下溃不成军,四处奔逃。团长李全山眼见形势不妙,无力回天,遂向川军第4旅旅长袁国瑞紧急求援。然而,袁国瑞彼时正被红军右路纵队逼得自保不暇,他仅淡淡回应道:“我们这里也很紧张”,便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李全山见状,意识到若不迅速撤离,将面临被彻底消灭的风险,于是立刻率领剩余的川军士兵迅速撤退。
红军仅耗时不到两个小时便成功夺取了泸定桥。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飞夺泸定桥行动中,二十二位勇士功勋卓著。在这二十二人中,有三名勇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其中,2连连长廖大珠,在一年后的陕北战役中同样壮烈殉国。
5月30日,继飞夺泸定桥的英勇壮举之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主力迅速抵达泸定桥,并随即展开了渡河行动。至6月2日,全体红军战士已顺利穿越泸定桥,成功跨越了险峻的大渡河。
红军转危为安。
叁 结束语
综上所述,这正是当年红军英勇飞夺泸定桥的壮丽历程。沿用惯例,我简略地总结几句。
众多人士心存疑惑,为何蒋介石命刘文辉炸毁泸定桥,而刘文辉却未执行此令?若桥身被毁,红军岂不面临绝境,难以逃脱?因此,有人据此推断,刘文辉可能有意放过了红军。
想多了。
刘文辉,身为一位地方军阀,内心实则矛盾重重。他深知不敢触怒蒋介石,因此在蒋的严令督促下,亦不得不部署重兵围剿红军。然而,他亦忧心忡忡,生怕红军难以渡过大渡河,届时红军将在川康之地久驻。若红军持续对其施压,蒋介石自会趁机插手川康,到那时,他这位西康王或许就得提前卸任退隐了。
因此,他的心思同样清晰明了:倘若老蒋能够将红军尽数剿灭自是上策;若非如此,便唯有祈愿红军得以借道通行,切莫滞留在自己的地界即可。
关于泸定桥,若你蒋某命令我将其炸毁,我便照办。但炸毁后,难道要我自己负责重建?而你却可轻松离去,而我却需依赖此桥维生。
泸定桥的建造可追溯至康熙年间,其工程之艰巨,耗费了巨额的金银与众多劳动力。此桥是连接西藏与四川的必经之路,而川康地区曾是刘文辉的势力范围,摧毁它无疑是在自毁长城。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负责炸毁却不管修复,岂不是让自己成了替罪羊?
因此,刘文辉未对泸定桥实施爆破,并非有意放水于红军,实乃出于对这座桥梁的惜别之情。
无论刘文辉心中所想如何,他未曾采取炸桥的行动,而是以实际行动助红军渡过难关。鉴于此,我党亦铭记他的恩情,在抗战期间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建国之后,更是赋予他重任,他一度担任了林业部部长的职务。
刘文辉的兄长声名狼藉,乃四川地区赫赫有名的地主刘文彩。
总结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因素。
首先,我们常对红四团在飞夺泸定桥的壮举给予高度赞誉,却往往忽略了其右翼纵队的英勇表现。队的职能至关重要。事实上,由刘伯承与聂荣臻指挥的右路纵队,在向泸定桥进发的征途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数场激战中,我方成功地极大牵制了川军的兵力,致使川军部署在泸定桥的防线遭受严重影响。兵力并不多。
如图所示,刘文辉所指挥的24军主力已基本部署于大渡河北岸。若非右路纵队有效牵制,川军各部势必将齐聚泸定桥,其后果尚难以预料。

其次,火力优势显著。正如前文所述,红军在火力上对川军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占据了绝对的上风。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这构成了二十二勇士成功穿越桥梁的最关键前提。第三,川军的战斗力相对较弱。尽管川军在内战中历经多年,场面看似热闹非凡,实则缺乏真正的激烈拼杀。毕竟在众人的认知里,战争的本质是为了求得温饱,可你为了温饱而牺牲生命,这样的牺牲又何来温饱可言?面对红军那不顾生死、勇猛异常的战斗风格,敌方往往一经接触便迅速溃败。第四,军阀间的相互猜忌。蒋介石怀揣着蒋介石的独到心思,刘文辉则有着刘文辉的私密考量。
心思细腻,却未能齐心协力。实则,红军之所以能从瑞金跋山涉水直至抵达陕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相互猜忌与制衡。
红军的胜利并非偶然得来。在诸多客观条件之外,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红5团在树种堡实施佯攻渡河,为红1团在安顺场成功强渡大渡河提供了关键保障;而采取的两面夹击战术,亦确保了飞夺泸定桥战役的最终胜利。红4团在一昼夜之内强行军240里,这一壮举更是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洞悉了这一切,便不难明白,为何如此微弱的军队,在国民党军强大的围剿封锁之下,竟能屡次化险为夷,最终在十四年后赢得最终的胜利。
历尽苦难,永不屈服。
怎么才能让配资公司破产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